找回 “虎刺”
◎克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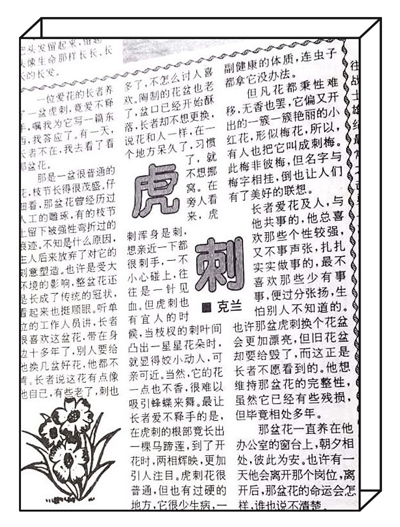
人过了一定年龄,往往会变得恋旧,各有所好、乐此不疲!恋旧是一种时光“穿越”现象,让人从过往时光里寻回丢失的“当下”,弥补岁月留下的“漏洞”,成为一些人积攒生命能量的隐秘路径。而我,偏喜欢将自己发表的文字作品做成“剪报”留存,权当是一种深情回望吧!
退休后的第一个春天,我开始编写《读书与写作年谱》,陆续发现有几篇作品被“剪报”遗漏,部分发表时间和责任编辑亦记录不全。其中,有一篇我尤为看重的小品文,专为一位老同志而写——他养的一盆虎刺花,随其辗转数个部门,愈发生机盎然,十分讨喜,唯独花盆老旧不堪。是否换盆?老同志始终犹豫不决,直到花盆酥裂破碎,才被下属趁机换上新盆。那种患得患失的心境难以言喻,只能用心体味,于是我写下《虎刺》一文,至今记忆犹新。
然而,疏忽造成的信息断层,给岁月留下一段“空白”,为年谱增添了一处“漏洞”,这让认真恋旧的我不免自责。
为弥补这份缺憾,我傍晚坐上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的火车,清晨便抵达这座熟悉而陌生的山城。途中邂逅一位老友,他带我到客运站大门旁的风味小吃店,点了一份包尔萨克、两碗奶茶和两碟小菜。饱腹之后,我直奔报社,一心想在资料室寻回“剪报”中遗漏的文章,之后便安心地走亲访友。
走进报社资料室,外屋陈列着具有纪念意义的报纸特刊、老照片等物件,俨然一座微型“史馆”,里屋的架子上,各年份合订本整齐排列,像是在静默中等待着与某段记忆重逢!我开始逐本翻阅1996~2002年的合订本,顺利找回几篇缺失文章,并意外发现两篇早已遗忘的特稿,但《虎刺》始终不见踪影。
“报社搬了几次家,资料室也改造过,库存资料搬来搬去,难免有散失。”朋友如是解释。
我深以为然:单位搬迁时,最不受待见的便是书籍报刊资料,吃力又不讨好。此时,收废品的往往闻风而至,得失就在那一会工夫。
我执意要找到《虎刺》,朋友建议去宣传部资料室碰碰运气。次日上班后,我便走进熟悉的办公大楼,工作人员热情地将我引入资料室。一个多小时过去,直到翻完最后一张报纸,仍未见《虎刺》。
为难之际,我突然想到或许图书馆、档案馆会有留存,便抱着一线希望赶往地区档案馆。为节省时间,我再次梳理《虎刺》写作与发表的时间线,确定文章应刊登于 2001 年四五月间。
馆员去地下书库不到十分钟,便将合订本轻轻搁在了会议桌上。我屏息凝神,逐页翻阅,终究在4月29日的报纸上找到了《虎刺》。我掏出手机,拍下其“固守一隅”的版面,确认清晰可辨后,顿觉一件大事终得圆满,时光“漏洞”也被填上了。我连声向馆员道谢,真心钦佩其高效精准的业务能力。
也许有人会疑惑——为一篇旧文,从乌鲁木齐跑到阿勒泰,这般费时费力,值得吗?在旁人眼中,这是“费事”,在我看来却是一场珍贵的“恋旧”之旅。往事并不如烟,过往岁月因为“恋旧”而得到充实,甚至复活!
这场寻文之旅让我看见:在阿勒泰的市井角落,总有一群人在默默坚守岗位、坚守初心;也让我不得不思索——一个地方或单位在迅猛发展变化中存在的“隐忧”,但愿寻找《虎刺》的经历能如虎刺花一般,无论环境如何变迁,都能激发人们于坚守中保持向上的力量。





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