品读新疆丨风沙三角地

品读新疆
走进新疆
去感触新疆
用你那一双赤诚的双手
去触摸166.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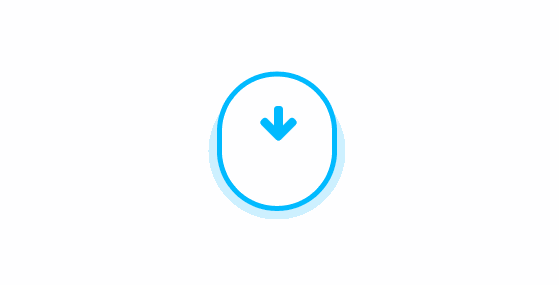
点击音频收听《风沙三角地》
汽车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戈壁滩上颠簸良久,当荒凉渐渐褪去时,轮南镇便像一块嵌在黄沙中的锈铁,显出了轮廓。从轮南镇一直向南50公里,便是西北油田知名的三角地。
此时的三角地,刚刚经历了一阵沙尘暴的侵袭。沿街两旁的店铺,陆续拉开卷帘门或玻璃门准备营业,有店员正用扫帚清理门前厚厚的沙尘,掀起一股黄色烟雾。因为正是黄昏时候,三三两两穿红工服的石油工人,拍拍身上的灰尘,纷纷走进超市、小饭馆,开始一天中的休闲时光。
沙尘暴是南疆特有的标记。每次刮起来,遮天蔽日,犹如一堵黄色的沙墙扑面而来。正在现场施工的作业工人,迅速转移到值班房里,大家戏称“妖风”又来了。有同事曾回忆:几年前最大的一次沙尘暴,曾把现场停放的一辆皮卡车掀翻在地。近年来,随着固沙工程诸如“草方格”、植树造林的有序推进,沙尘暴没有以前那么凶悍了。

三角地是石油人对这个小镇的俗称。它位于轮台县轮南镇,小镇的奇特之处,在于它地处三岔路口,向北可通往轮台县城,向西可达塔河油田采油二厂和三厂,向东可到采油一厂及胡杨林公园,人们便顺口唤它作三角地。这里虽不及大城市那么繁华,但在浩瀚的大漠里,却是一个绝佳的去处。三条公路如同大地的创口,在此处交汇。这里有一条5公里长的南北向街道,宽不过10余米,两侧凌乱地坐落着饭馆、超市、汽修铺子等各式房屋,就像戈壁滩上的红柳,顽强地生根、聚集。它们低矮、杂乱,却构成了一处微缩的人间烟火,成为石油人短暂休憩、彼此取暖的驿站。
此地风沙粗粝,风云变幻莫测,早上还是朗朗晴日,白云朵朵,傍晚便刮起沙尘暴。风沙掠过三角地那些简陋的招牌时,发出呜咽似的声响。“巧味”面馆的老板娘初来时皮肤白皙,如今脸上也有了风沙的土黄色,她每日清晨擦拭店门玻璃,仿佛在擦拭着永无休止的时光印记。“师傅,进来坐嘛,还有空位!”她操着浓重的川音,招呼着来往的石油工人,那声音在风沙里显得格外熨帖,仿佛一碗热乎乎的面汤,足以温暖疲惫和烦恼。
三角地的人,都是被石油这股巨大的威力,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的。饭馆里终日烟气缭绕,天南地北的口音嘈杂地交织在一起,如同大漠里奇特的交响曲。

来自河南的修井工,嗓门洪亮,谈论着井下又使用了一套新工艺;四川的厨师,麻利地颠着炒勺,锅里的火焰腾起又落下;烧烤店里的“巴郎子”,用红柳枝穿起大块肥美的羊肉,炭火烤出滋滋的声音,烟火缭绕;东北大姐,手捏面皮,熟练地包着酸菜馅饺子……他们口音各异,却都带上了一种粗粝的质地。这风沙,如同无形的熔炉,将异乡人不同的音调渐渐熔铸成了此地特有的腔调——一种带着石油气味的、沙哑的、被风打磨过的口音。
这三角地,亦是各种生计的角力场。老孙的汽修铺子,终日弥漫着浓烈的机油与尘土混杂的气息。他干枯的手上布满油污,却异常灵活。无论多棘手的故障,他俯身钻到车底,捣鼓一阵,便能让那些钢铁巨兽重新发出低吼。他常念叨:“这些铁家伙,就是咱油田的腿脚,瘸不得。”铺子一角,堆满了报废的零件,层层叠叠,无声诉说着风沙与钢铁之间无声的鏖战。
吕老板是三角地的“石油通”。她是一位30多岁的东北大嫂,微胖,心直口快,与老公分别开两辆车,一辆拉客人,一辆运送工具。她每天驾驶着一辆带拖斗的皮卡车,迎着沙尘,在修井队与施工队间穿梭,给工人送饭、送配件。抽空还要拉几位熟客,往返于三角地与县城之间,顺便挣点外快。“这儿方圆数百里的每口井,我都门儿清,穿过几个沙丘,绕过几片胡杨林,我记得老清楚了。”她说。

三角地的存在,仿佛只为着这些整日劳作的石油工人。白日里,工人们上班,小镇便显出几分空寂。只有那些小店,沉默地守着,如同搁浅在沙滩上的小舟,等待着涨潮。黄昏,巨大的日轮沉向戈壁尽头,将钻塔的剪影拉得如同巨人般投向大地。这时,下工的车辆才如归巢的倦鸟,裹挟着一天的疲惫与喧嚣,重新涌入三角地那并不宽敞的街道。
三角地向东,便是西北油田采油一厂的驻地。在沙枣树、杨柳树的掩映下,办公楼、公寓和食堂等建筑错落有致地排列着。这里有散发着芳香的葡萄长廊,还有盛开着百日菊、栀子花的花坛。每天早上,数十辆车从这里出发,开往方圆数百平方公里的生产现场,处理各类与油气相关的业务。傍晚时分,便有一辆小面包车,拉着一些工人前往三角地取快递、理发或是购物,那里又开始热闹起来了。
“沙核”奶茶店位于三角地进口位置,与车站毗邻。此时霓虹灯开始闪烁,在沙尘弥漫的夜色里显得格外突兀,又带着一种奇异的召唤力。年轻人是这里的主角,他们脱去沾满油污的工装,换上干净的衣服,聚拢在小店里。空气中弥漫着甜腻的奶香。店主是个江苏小姑娘,头戴棒球帽,眼神明亮,熟练地摇动着雪克杯,冰块撞击杯壁发出清脆的声响。一杯杯色彩缤纷的奶茶递出,暂时消解了戈壁的单调与漫长。角落里,有一位年轻的石油工人,穿着带油污的红工衣,对着手机屏幕,压低声音和远方的恋人视频通话,脸上带着温柔笑意。这小小的奶茶店,竟成了风沙线上一处闪着微光的、甜蜜的栖息地。

深夜,当最后一拨食客打着饱嗝离开“四川菜馆”,老板娘熄了灶火,开始打扫一地狼藉。隔壁超市的老张正借着门口昏黄的灯光,清点着货架,盘算着明日要补的货。唯有老孙的汽修铺还亮着一盏孤灯,他佝偻着背,仍在灯下敲打着零件,那叮叮当当的声音,在沉寂下来的三角地里传得很远,如同小镇最后的心跳。
我离开三角地的那天清晨,风沙又起,天地昏黄。一辆载着休假工人的班车,如同移动的堡垒,冲破风沙,驶向300公里之外的库尔勒。车窗外,那些低矮的店铺,渐渐模糊渺小。然而,就在这混沌的底色上,“沙核”奶茶店那鲜亮的招牌,却依然亮着光,像一枚倔强的火种,在风沙中兀自燃烧。
这三角地,不过是浩瀚戈壁滩上微小的一粒芥子。它是如此简陋、粗粝,被风沙日夜啃噬,被石油浸染。可它又如此坚强,收容着疲惫与风尘。当车轮卷起沙尘,三角地终于消失在我身后苍茫的戈壁中,那些混杂着机油味、饭菜香、奶茶甜腻气息的记忆,却总是令人挥之不去。
文/孔守曾


















